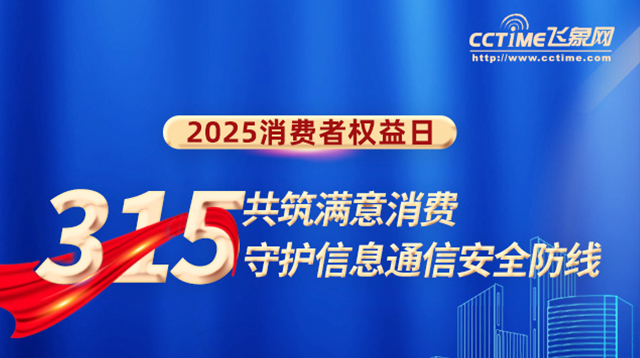飛象原創(孫迎新/文)誰能想到,低空經濟強勢啟動的信號就像春天里的這陣風,來得又快又猛,讓人有點猝不及防。2025年3月31日,合肥合翼航空的辦公室里應該是一片歡呼,中國民航局向合肥合翼航空頒發了全球首張民用無人駕駛航空器運營合格證(OC)。

這張“空中駕照”不僅讓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eVTOL)載人服務從實驗室走向街頭巷尾,更標志著低空經濟正式開啟了商業化的大門。這個標志性時刻的真實含義,就如億航智能創始人胡華智所言:“我們正在打開一扇通向未來的門,門后是一個立體的、充滿想象力的新世界。”
就在此刻的大洋彼岸,墨西哥城上空,一架EH216-S電動飛行器輕盈掠過,20分鐘的跨城飛行讓乘客驚嘆“科幻片場景成真”。這架由億航智能研發的“空中出租車”,正是全球首個獲得適航認證的載人eVTOL機型,正搭載著兩人,以200千米/小時的速度,飛過墨西哥城盛開的藍花楹。它的商業化運營,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低空經濟從政策試驗田走向產業深水區的里程碑。
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低空經濟規模突破5000億元,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飆升至2萬億元。市場的爆發性增長背后,是政策、技術、資本的三重共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范恒山指出:“低空經濟正在重構生產要素的流動方式,它不僅是交通工具的革命,更是生產關系的顛覆。”
政策東風下的產業狂飆:30省競逐“天空之城”
低空經濟的崛起,始于頂層設計的破局。2024年,“低空經濟”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標志著這一新興產業正式納入國家戰略框架。隨后,《通用航空裝備創新應用實施方案(2024-2030年)》明確提出,到2030年形成萬億級市場規模,推動“低空+物流”“低空+交通”等場景規模化落地。
政策的齒輪一旦轉動,便引發全國30個省份的競速:廣州計劃2027年低空經濟規模突破1500億元,深圳宣布建設1200個起降點,湖北憑借通航飛行小時數中部第一的優勢,力爭打造“低空經濟走廊”。
“誰能搶占低空經濟制高點,誰就能贏得未來十年的城市競爭。”深圳市發改委高屋建瓴,一語道出了全國30個省份將低空經濟寫入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的深層邏輯。從北京投資千億打造“低空智聯網”,到浙江紹興豪擲20.5億元建設全域低空新基建項目,一場關于“立體空間”的爭奪戰已然白熱化。
爭奪戰中,政策的調控之手精準而有力:專項債資本金比例提升至30%,重點投向通用機場和空管系統;《無人駕駛航空器飛行管理暫行條例》終結“黑飛”亂象;工信部等四部門聯合印發《通用航空裝備創新應用實施方案》,劍指萬億級產業集群。
在這股政策東風下,企業軍團快速集結:萬豐奧威的“eDA40”電動飛行器亮相珠海航展,寧德時代研發的航空級固態電池能量密度突破400Wh/kg,臥龍電驅的航空電機讓飛行器續航提升30%。這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出政策的作用立竿見影,正如中國民航局原總工程師殷時軍所言:“政策不是畫餅,而是實實在在的產業催化劑。”
這場“天空爭奪戰”的背后,可以升格為地方政府對生產要素立體化重構的深刻認知。全國政協委員付誠指出:“低空經濟不僅是交通方式的升級,更是城市空間資源的再分配。”而這場天空爭奪戰各地早已用自己的方式開啟:紹興投資20.5億元建設全域低空新基建,7個大中型起降場與50個微型站點構成的網絡,將文旅觀光與應急救援無縫銜接;而深圳依托5G-A通感一體化基站,實現無人機航線規劃與飛鳥軌跡追蹤的“數字交警系統”,則展現了技術賦能的無限可能。
技術突破與基建狂潮:編織立體中國的“天空路網”
技術的突破,是低空經濟騰飛的核心引擎。就以其中的一些略顯“跨界”的技術為例,億航智能的EH216-S是全球首個獲得適航認證的無人駕駛載人eVTOL,其碳纖維機身與低噪音設計,重新定義了城市空中交通的可行性;光啟技術研發的超材料飛行汽車葉輪,將風阻降低40%;萊斯信息開發的智慧空管系統,讓飛行調度效率提升3倍。
看到這么多井噴般的創新成果,就連中國工程院院士劉大響都深發感慨:“這是中國制造業的二次覺醒——從地面到天空,我們正在重寫游戲規則。”
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技術鏈的完善,催生了產業鏈的裂變。我國民用無人機產業規模已超1200億元,全球市場份額占比60%,大疆、極飛等企業占據消費級與農業無人機市場絕對優勢。而在eVTOL領域,峰飛航空的“盛世龍”完成深圳至珠海跨海首飛,將地面2小時車程壓縮至20分鐘,展現出商業化應用的巨大潛力。
特別應該注意的是,領先通信技術的應用讓無人機飛行器的飛控管理邁上了一個更高的臺階。在深圳人才公園,中興通訊與中國移動打造的5G-A通感一體化基站正全天候掃描方圓1.5公里空域。這套系統不僅能追蹤飛鳥軌跡,還能為無人機規劃最優航線,其定位精度達到驚人的亞米級。“我們正在建造數字時代的‘空中交警系統’。”中興通訊無線未來實驗室主任崔亦軍的比喻,揭示了技術突破與基建協同的深層邏輯。
此外,技術的狂飆也需要基建的支撐:深圳計劃2026年前建成1200個起降點,浙江規劃150個公共無人機起降場,上海建工在紹興建設的7個大中型起降場已初具雛形。這些“空中驛站”如同星羅棋布的節點,串聯起低空經濟的神經網絡。
場景革命與區域競合:從“送外賣”到“打飛的”
如果談及低空經濟的魅力,首當其沖在于其重塑社會運行的穿透力。在深圳,美團無人機日均完成超700單配送,風雨無阻地將咖啡、藥品送至用戶手中;在自貢,無人機搭建的“低空生命線”實現血液樣本1小時跨城轉運,挽救無數危急病患。這些場景的背后,是技術與社會需求的精準耦合:順豐構建“三段式航空物流網”,干線大型運輸機、支線無人機與末端配送機協同作業,大灣區1-3小時送達網絡已成常態。
低空經濟場景革命更深遠的影響在于公共服務升級。中航工業“翼龍”無人機在西藏地震中穿透高原極端氣候,實時傳回災情數據;武漢銳科光纖開發的激光雷達技術,讓無人機在電力巡檢中精準識別毫米級設備缺陷。就連全國政協委員羊毅都在感慨:“低空經濟讓‘空中之城’從科幻走入現實,它不僅是交通工具,更是社會治理的智能觸手。”
作為低空經濟應用場景的“傳統勢力范圍”,在安徽黃山風景區,順豐無人機日均運輸物資20噸,徹底解決了索道運力瓶頸;在湖南湘西,游客花500元即可體驗“穿越云端”的低空觀光;在廣東湛江,京東物流的無人機將生鮮準時送達海島漁村……這些看似零散的場景,正拼湊出低空經濟的全景圖。
與低空經濟應用場景對應的另一個維度,在區域競爭的硝煙中,差異化戰略也逐漸清晰:合肥依托中科大科研優勢打造“中國低空硅谷”,深圳憑借完備的電子產業鏈孕育出大疆、億航等巨頭。這種競爭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同做大產業蛋糕的必然路徑,而這個思路也適合大部分的城市,正如北京市經信局提出的:“每個城市都應該找到自己的‘空中名片’。”
這些名片反映出的是低空經濟的蓬勃發展,也是各自城市競爭的立體化轉型。北京依托中關村科研優勢,打造“創新主導型”模式;杭州以電商物流需求反哺技術研發,構建“需求驅動型”生態;成都則聚焦“低空+文旅”,開發大熊貓主題觀光航線,單次飛行體驗票售出超10萬張。這種差異化戰略,同時也避免了“一哄而上”的資源浪費,正如全國人大代表吳仁彪所警示的:“低空經濟需要因時因地制宜,條件不足的地區盲目跟風只會‘滿地雞毛’。”
如果把區域競合的目光聚焦到低空經濟發展的“敏感區”,則還能看到更多的成功案例:粵港澳大灣區憑借完備的產業鏈,成為全球低空經濟的試驗田,這里既有億航智能的載人飛行器,也有順豐的物流無人機網絡,更有深城交打造的“低空數字底座”,這是一個覆蓋起降點、通信導航與監管服務的智能系統,支撐1000架航空器同時飛行。
看著如此豐富而又立體的物流交通模式,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副會長呂本富將其概括為“五流合一”:高鐵、公路、水運、航空與低空經濟協同,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立體交通范式。在此我們也應相信,粵港澳大灣區這塊試驗田用不了多久,就會成為全國乃至全球低空經濟發展的標桿。
未來挑戰:破解“天空密碼”的三重關卡
盡管前景光明,低空經濟仍面臨難以回避的“成長煩惱”。在湖北,通航機場網絡尚未形成聯動,空域審批周期長達數月;在延慶無人機測試基地,技術人員為避開民航航線不得不將試飛時間壓縮至凌晨;在西部某山區,價值千萬的巡檢無人機因通信網絡覆蓋不足淪為“擺設”。這些案例暴露出三大核心挑戰:
空域管理的“玻璃天花板”——現有空域開放高度多限制在300米以下,而eVTOL理想作業高度為500-1000米。中國民航局空管局副局長顏曉東坦言:“我們需要在安全與發展間找到更優解。”
基建短板的“木桶效應”——三四線城市起降點覆蓋率不足20%,5G-A網絡部署進度參差不齊。基建方面的短板是低空經濟發展的硬傷所在,應該認識到,沒有5G-A等先進“地網”的支撐,低空經濟的“天路”就是空中樓閣。
國際競爭的“標準博弈”——歐美正加緊制定eVTOL適航標準,試圖建立起屬于西方話語權的技術壁壘。我們應重視起標準的力量,盡管在無人飛行器技術方面,我國早已走在世界前列,但也要警惕陷入“起了大早,趕個晚集”的被動局面,也正如峰飛航空副總裁謝嘉所直言的:“我們要用中國標準定義未來空中交通。”
展望將來:當“中國翅膀”舞動全球天空
現在回頭再看,很多低空經濟的概念早已演變為觸手可及的現實,而政策、技術、場景的三重突破,正在催生一個立體的、數字化的新經濟形態。這個萬億級市場不僅將重塑城市空間格局,也或將孕育出全新的生活方式:早晨,上班族們可以乘坐便捷的飛行汽車跨城通勤;中午,無人機為在寫字樓里勤奮工作的“牛馬”們送來熱乎乎的午餐盒飯;傍晚,各種飛行器在黃昏中穿梭的身影成為妝點城市地平線的靚麗風景……

低空經濟未來可期,當中國的eVTOL機型開始出口海外,當“低空智聯網”標準成為國際范本,當每個縣城都擁有自己的“空中物流站”,這場奔赴萬億藍海的征途也終將為我們拓展出一個全新天地,就如中國科學院院士李德仁所說:“低空經濟的終極目標不是替代地面交通,而是創造人類活動的第三維度。”